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严重转折含义的历史时期,各种学术思潮异常活泼,在新的年代环境中奇光异彩。《周易》在取得两汉经学的青睐后,又开端阅历魏晋形而上学的洗礼。形而上学化的《周易》学派蔚然兴起,锋芒毕露;一起,由于动荡社会的实际需要,依托《周易》的卜筮也广为传达,向社会作立体化、多方位的渗透。东晋是一个形而上学兴盛、文艺繁荣的年代,全面考察《周易》的传达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,关于丰厚易学史研究、加深对东晋文艺的了解都是不无裨益的。
《周易》首要传达方法
通过官办校园讲授是《周易》直接传达的首要方法。王弼易学在东晋遭到推崇并广为传达。《北史•儒林传序》云:“江左,《周易》则王辅嗣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序录》云:“江左中兴,《易》唯置王氏博士。”东晋初建,元帝修正校园“公卿子弟,并入国学”“简省博士,置《周易》王氏……郑《易》皆省不置。” 荀崧为此曾上疏力求将郑玄易学置博士一人。元帝令臣下博议,臣下
皆认为可,元帝准奏。但“会王敦之难,不行”,不了了之。查《晋书》不见有再置郑玄《易》为博士的记载。因而,很可能直到梁、陈年代才有“郑玄、王弼二注列于国学”一”。王弼《易》注既然列于国学,当然也就成了学生的考试科目。据《晋书•孔坦传》,东晋建立三年后,针对各地举荐上来的秀才、孝廉,晋元帝“申明旧制,皆令试《经》”,后听取孔坦建议,仅定孝廉四年后试《经》,秀才则仍依旧制。
除了国学,当地校园也是《周易》传达的重要场所。《通典》卷五三云: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时,开办官学,“近临川、临贺二郡并求修正校园”。⑷可见,当地官学随着形势的稳定,也逐渐得到康复或新建,包含《周易》在内的儒家经典自然成了首要科目。在当地上办学影响*大的当数豫章太守范宁,他“在郡大设庠序”,“远近至者千余人”,“并取郡四姓子弟,皆充学生,课读《五经》”。这些校园培养了一大批通晓《五经》的学生。如《宋书•周续之传》云:周续之“年十二,诣宁受业,居学数年,通《五经》并《纬》、《候》”。《晋书•许孜传》赞许孜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,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”。当然范宁答应讲授的极可能不是王弼《易》学,由于他宗尚传统儒学,痛恨浮虚玄风,并认为这种学风“源始于王弼、何晏,二人之罪深于桀纣”,作专文驳斥王、何“游辞虚说” 。
私家传授也是东晋《周易》直接传达的一种重要方法。私家办学行之有效和声名的是范宣,《晋书•范宣扬》称“江州人士并好经学”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讲习之功。他“博综众书”,所著《易论难》撒播当时。据《晋书•郭璞传》,郭璞受业于“旅居河东”的郭公,郭璞也曾私家授学,因而本传称郭璞“门人赵载尝窃《青襄书》”如此。被列入《晋书•艺术传》的东晋术士,多有学于私门或私家授徒者:
步熊,字叔罴,阳平发干人也。少好卜筮法术,门徒甚众。
杜不愆,庐江人也。少就外祖郭璞学《易》卜,屡有验。
韩友,字景先,庐江舒人也。为墨客,受《易》于会稽伍振,善占卜。
《周易》传达所及,不止限于儒生,佛教徒也莫能破例。如竺法太的弟子“昙一、昙二,并博练经义,又善《老》、《易》,风流趣好,与慧远齐名”慧远一代宗师,“少为诸生,通《六经》及《三藏》” 通晓《易》理。僧“通《六经》及《三藏现存支遁诗文中屡次运用《周易》概念语词。和尚接受《周易》首要不是阐发易理,而是与佛理相印证,或许以易解佛。如释道立“以《庄》、《老》三玄,微应佛理,颇亦属意焉”。支遁作《释迦文佛像赞序》云:
冲量弘乎太虚,神盖宏于两仪;易简待以成体,太和拟而称邵;圆蓍者像其神寂,方卦者法其智周。
这哪里是释迦大佛,实在是《周易》太极的神像。慧远《沙门不敬王者论序》云:“岂独以圣人在位,而比称二仪哉!”于《出彖二》云:“故凡在落发,皆豹隐以求其志……豹隐则宜髙尚其迹。”这是借时人熟悉的《周易》之理为佛教徒的生活方法和价值寻求作证明。由此足见和尚中的贤智之士于《周易》修养之一般。
清谈是《周易》在上层名流中传达的一种重要方法。作为“三玄”之一,《周易》是东晋名士的案头必研书,通易理是风流拔俗的基本标志。《晋书•王湛传》载:
(王)济尝诣湛,见床头有《周易》,问曰:“叔父何用此为?”湛曰:“体中不佳时,脱复看耳。”济请言之。湛因分析玄理,奇妙有奇趣,皆济所未闻也。济才气抗迈,于湛略无子侄之敬。既闻其言,不觉栗然,心形俱肃。遂留连弥曰累夜,自视缺然,乃叹曰:“家有名士,三十年而不知,济之罪也!”
《周易》是王湛的“床头”书,其侄王济“何用此为”的问句,于嘲笑中透出这样的信息:只有名士才读《周易》。王济于王湛处“留连弥日累夜”,清谈《周易》义理当是重要论题。
清谈《周易》,有时是一人清言,如上段引文中王湛“清言”,即自己一人论述《易》理,因而说“济所未闻也”。《世说新语•文学》云:
宣武集诸名贤讲《易》,日说一卦。简文欲听,闻此便还。曰:“义自当有难易,其以一卦为限邪?”
桓温说卦是一人讲,世人听。因讲法呆板,引来简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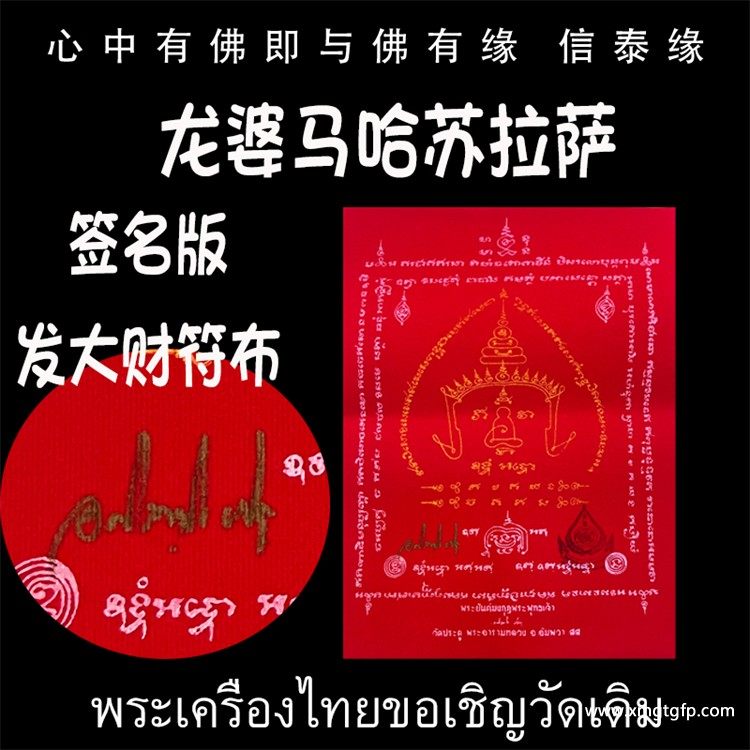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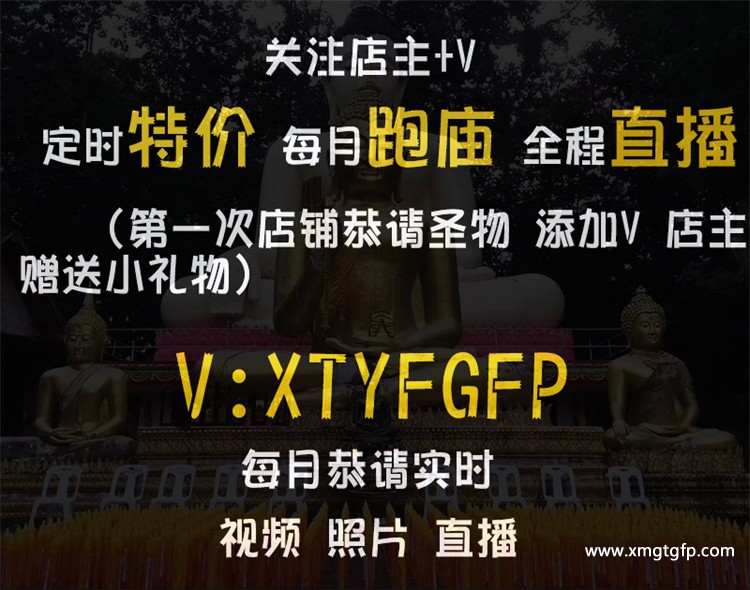
 在线客服
在线客服



 在线客服
在线客服